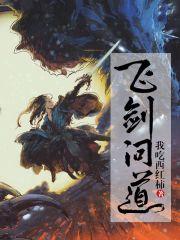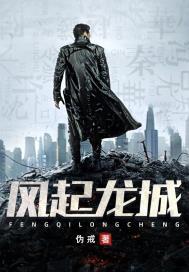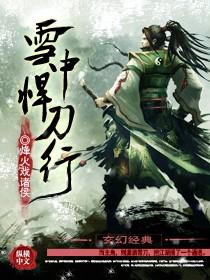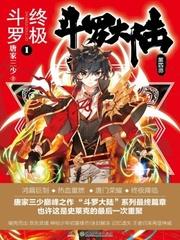蜜汁中文网>红尘修道录

红尘修道录
无系统+无穿越+凡人流+历史玄幻+传统仙侠+功法描述+修行启迪林清扬生于嘉靖三年秦岭深处,天生“白玉体”,自幼梦见星空与白发老者指引,注定不凡。十二岁拜游方道士李散人为师,开启修行之旅。小说以其成长为主线,融合历史事件(嘉靖朝政、张居正改革、明朝灭亡、清军入关和崛起)与仙侠世界,讲述他从一阳生到金丹、元婴、化神,最 红尘修行:证道之路
《红尘修道录》第215章 文明方舟书海初成
了近月才得以恢复。那位宁死护书的寒士,名叫孙传庭,乃是一位因言获罪的翰林学士。我将他送至最近的边陲小镇,留下些许银两丹药,便悄然离去。他并未问我的来历,我也未言明去向,只是在那临别的一揖之中,彼此都已明了,那份属于读书人的薪火之传,已然交接。 我没有再继续西行。 西北的苍凉与风骨,已尽数烙印于心。我转而南下,入蜀,过湘,再至岭南。这一路,我不再刻意寻访那些名山大川的藏书之所,而是将更多的目光,投向了那些散落于乡野阡陌的,最不起眼的“文字”。 我曾在川蜀的崇山峻岭之中,从一位老猎户的口中,记录下早已失传的百濮山歌;也曾在洞庭湖畔的渔村里,听一位说书的老者,弹着三弦,唱起那段关乎“君山银针”的古老传说。我甚至在岭南的市舶司,从那些远渡重洋而来的番商手中,...
《红尘修道录》最新章节
- 第215章 文明方舟书海初成
- 第214章 风雪西北墨卷埋沙
- 第213章 藏经洞府佛音浩荡
- 第212章 民间私藏血火守书
- 第211章 文人故宅墨香犹在
- 第210章 皇室秘库风雨入夜
- 第209章 踏遍江山寻书启程
- 第208章 陪同历练惊闻噩耗
- 第207章 再上龙虎介绍弟子
- 第206章 急赴白马寺僧人进京超度
- 第205章 京师惊变付诸实施
- 第204章 京师惊变深入虎穴
《红尘修道录》章节列表
- 第1章 月引奇境机缘
- 第2章 故乡余韵初试锋芒一
- 第3章 故乡余韵初试锋芒二
- 第4章 黄风暗藏灵果因缘
- 第5章 修行入门丹田气海一
- 第6章 修行入门丹田气海二
- 第7章 意外邂逅殷切期望
- 第8章 星枢启阵红尘劫起
- 第9章 紫阳观惊变白马寺因缘
- 第10章 龙虎山中风云变紫霄宫内觅真言一
- 第11章 龙虎山中风云变紫霄宫内觅真言二
- 第12章 龙虎山中风云变紫霄宫内觅真言三
- 第13章 星移斗转三月将至
- 第14章 晋王府暗流涌动
- 第15章 星枢异变心魔暗生
- 第16章 群雄汇聚博弈暗藏
- 第17章 推测真相张天师定策
- 第18章 迷宫幻阵步步惊魂
- 第19章 核心交锋智斗难分
- 第20章 龙虎血战群阵暗启
- 第21章 母蛊殒地祭坛崩坏
- 第22章 心魔暗战无我破障
- 第23章 归来与闭关
- 第24章 准备初探红尘
- 第25章 鹰潭启程初窥红尘
- 第26章 鹰潭小二的奇遇
- 第27章 医者仁心驱邪护道
- 第28章 书院初探儒道交融
- 第29章 心学之辩
- 第30章 山村遇险夜探坨坨寨
- 第31章 计中计智斗南霸天
- 第32章 金陵道观暗流涌动
- 第33章 祈雨之恩黑风岭的秘密
- 第34章 顿悟之悟金丹中期突破
- 第35章 帝王之礼与别离
- 第36章 裕王府叙缘起天机
- 第37章 秋风练功张氏来访
- 第38章 暗影低语
- 第39章 天师援手满月将至
- 第40章 龙脉之战满月危机
- 第41章 罗天大醮与龙珠北踪
- 第42章 酒肆论道国之根基
- 第43章 红尘烟火道在人心
- 第44章 红尘历练布庄偶逢
- 第45章 京师暗流北上之议
- 第46章 疫村哭嚎符光驱邪
- 第47章 严党追兵山道血战
- 第48章 梦中指引因果初现一
- 第49章 梦中指引因果初现二
- 第50章 荒野笛声莫玄挑衅一
- 第51章 荒野笛声莫玄挑衅二
- 第52章 荒野谋策静待援军
- 第53章 北上探秘误入魔渊
- 第54章 血鸦围困生死抉择
- 第55章 星图传承金莲渡厄一
- 第56章 星图传承金莲渡厄二
- 第57章 重聚惊变梵音破障
- 第58章 古剑冢剑灵泣血
- 第59章 熔岩狱生死抉择
- 第60章 休整与疑云
- 第61章 药神传人往事秘辛
- 第62章 九幽潭往世镜
- 第63章 毁坛唤兽
- 第64章 正道营救一线生机
- 第65章 修为暴涨
- 第66章 逃离魔渊
- 第67章 再遇阿福重上龙虎
- 第68章 烟雨调息急进京师
- 第69章 京师故友古庙仙踪
- 第70章 光明追兵意斩群敌
- 第71章 江南游历黄山悟道
- 第72章 九华佛光愿力初现
- 第73章 武当问道太极真意
- 第74章 北上风云情缘了结
- 第75章 救民水火愿力再现
- 第76章 星空指引北上泰山
- 第77章 泰山仙鹤灵羽赠礼
- 第78章 昆仑初探遗骨安葬
- 第79章 江南归途民生百态
- 第80章 再会张居正改革暗流
- 第81章 山西卖糖初春之像
- 第82章 双侠仗义改革初启
- 第84章 俩女天赋武台修行
- 第83章 光明阴谋商贾通敌
- 第85章 再遇流氓巧治阔少
- 第86章 阔少修渠因果牵引
- 第87章 白马寺论策入川寻道缘
- 第88章 险峰风光奇遇秘境
- 第89章 秘境中突破团队收获满满
- 第90章 青城聚会共享秘境
- 第91章 人间繁荣愿力如海
- 第92章 冯保疑云暗流再起
- 第93章 回乡探亲俗世难免
- 第94章 红尘修行俗事筹备
- 第95章 药堂成功巧遇弟子
- 第96章 张凌拜师冯保暗影
- 第97章 陈默归附药道初现
- 第98章 柳如烟入道符箓天赋
- 第99章 弟子初战光明挑衅
- 第101章 弟子历练声名鹊起